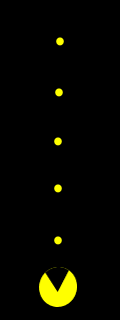| 都市消费晨报:与一个非典时期辞职医生的对话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25日16:42 都市消费晨报 | ||||
|
与天使背道而驰? 面对面——记者与一个辞职医生的对话 引语: 今年4月,在清理广东省中医院因抗击非典殉职的护士长叶欣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唐代名医孙思邈的中医巨著《备急千金要方》之首的《大医精诚》,这篇讲述医风医德的医古文就是叶欣1974年考上广东省中医院的“卫训队”正式从医所上的第一课:“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孙思邈提倡为医者必须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我们把他们叫做“白衣天使”。 这两年,有人动不动就骂医护人员、埋怨医院不负责任,甚至在今年发生的非典之前,追打医护人员的事仍然频频见诸报端。天使、医院该怎么与病人达到融合,这是日益尖锐的矛盾如何消除?天使们该如何面对这个职业? 今天,我们面对面与一位刚刚从医生岗位上走下的普通人交流,他从学医到从医11年,他马上就可以从住院医生升为主治医生了..........他一度非常钟情于医生这个职业,但他辞职了。即使已经离开医院两个月,他仍把印有医院标志、编号以及自己照片的工作胸牌放在钱包夹层里,到北京出差也带在身边。 本报记者马金瑜 晨报讯:7月22日上午,30岁的周伟峰再次来到自治区中医院,试图说服一些医生购买“好医生”网站的学习卡。没有人再叫他“周大夫”,以前的同事看见他,略一点头,态度显然很冷淡。周伟峰曾经在这里工作了六年,但现在他已经不属于这里了。两个月前,也就是5月末,在防非典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他从医院辞职了。记者是在医院采访时了解到这一消息,在第一次(7月18日)约见他的时候,他显得很吃惊,他急忙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医院的人是怎么说我的?”电话里传来的语气里显然有些紧张。当时,他正在北京接受新岗位培训。时隔两日,他答应了记者的采访。但,这次面对面交谈,他是带着妻子一块来的,他说,要慎重对待这次采访。 记者:今年前段时间,我曾多次到发热门诊采访,看到许多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为发热患者做检查和治疗。当时疆内出现疑似病例时,不少发热门诊连一个护工都招不来。你在这时候走,不觉得自己是个逃兵吗?请原谅我用“逃兵”这个词,可能不太礼貌。 周伟峰(眼睛望着桌面,一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你问的问题让我很惭愧,这可能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现在回头想想,如果我当时不提出辞职,因为业务能力比较强,我很可能是我们医院干一科第一个被抽调到发热门诊或者疾控中心去的医生。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是个逃兵吗?”我无法回答自己,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我学医和从医的这11年里,我没有愧对这个职业,我是热爱这个职业。当时“好医生”网站在新疆要招一名学术推广专员,机会很难得,时间恰好赶在那个时候,做这个抉择很难,也让我很痛苦,那段时间我回家很少说话。辞职手续已经办完了,但我接诊的几个病人还在科里住院,我不放心我的病人,一直坚持工作到最后要去网站上班的时候。 记者:你的说法很矛盾。既然你是热爱它的,为什么又在最需要履行医生救死扶伤职责的时候离开呢?这和你最初学医时的想法一致吗? 周伟峰(眼睛直视记者,边说边打手势,有点激动):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是一个工人,你修理1000台机器,有999台修好了,有一台被你越修越坏,甚至修得不走了,你会因此挨揍吗?你会丢饭碗吗?你会因此成被告吗?会坐牢吗?——医生会!我父母当初很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为良相,宁为良医”,在我眼中,医生也的确是个很好的职业,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但是这份职业的压力很大。记得我当急诊大夫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几乎就在几分钟之内,送来了4个病人,最重的已经昏迷,最轻的头部裂伤,需要缝合。而那个昏迷的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在那样的情况下,人的神经非常紧张,可是这样情况可能是每天都会有。就这样,有时还要受委屈。你精心为患者治疗,可他回头还要投诉你,说你没给他把病治好,你心里会好受吗?再者,医学是个飞速发展的学科,想不被淘汰,医生只有不断看书、看书、再看书,医院还要不断考试、考试、再考试。还有计算机、英语、操作等等的考试,这样还不行,医学本科生已经很多,硕士都在这个行业里算最低学历,你能不学吗?就算这样兢兢业业,还是有不少人骂医生!这公平吗? (喝一口茶,停顿了几分钟,低头沉思,双手放在膝盖上) 所以我辞职了,我是个普通人,我不高尚。我做现在的工作,跟过去一样累,一样不被人尊重,一样饱受非议,但我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我觉得够了,没有必要再苛求太多。这次非典,我的很多同学和从前的同事都站到了第一线。同他们相比,我惭愧。但我不羡慕他们。那段时间,我经常给他们发短信,我对他们只是祝愿,愿他们平安,也祝愿他们今后的人生如意。(眼睛望着窗外) 记者:在非典那个特殊时期辞职,你是不是招来很多非议?医院是什么态度? 周伟峰:应该说同事、朋友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了解医生这个职业,知道医生很辛苦也很冒险;也有人说我赚大钱去了,其实我现在的工资并不是很高,有时甚至还没科里的奖金高。因为我已工作了6年,马上就可以当主治医生了,还是很可惜的。院长和副院长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慎重地选择,但没有因为我在那时候提出辞职批评我。院领导还在那时候给我放了15天假,因为我一直没有休过年假,工作总是很忙。他们也都是学医出身,明白医生的心酸和难处,我很感谢他们。从科里走的时候,我把胸牌留了下来,(随手拿过包,从钱包夹层里取出以前的胸牌给记者看,照片上的周伟峰显然要比现在胖一些,而且比现在的皮肤要白得多)虽然它已经不能用了,但我走到哪里都常看看它,我还是老说我们医院如何如何,在感情上,我还是深爱着这个职业,爱着医院的。 (低着头看胸牌,看了两分钟左右,小心翼翼地把胸牌放回钱包夹层里) 记者:采访之前,你告诉我,辞职后,你还是很关注防非的情况,包括晨报当时架设爱心桥,开通可视电话,你们医院的医护人员现场接受采访等等,你都记忆犹新。当时为什么那么关注这些呢? 周伟峰: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的根还在医院,我还是医院的一分子,另一方面没有参加防非典一线的工作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或者说是从医生涯中最大的遗憾。如果我当时留下来了,也许那种经历是永生难忘的,是刻骨铭心的。 记者:现在我们能不能假设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好医生”网站没有招聘学术推广员,你还会不会参加防治非典一线的工作? 周伟峰: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反复想过多次。如果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医院不抽我去,我也会写申请书要求去一线工作。 但当时对非典疫情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也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而且我当时已经有了辞职的想法,心思已经不全在工作上,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去给病人看病,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对培养我的医院,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我个人也是有害处的。所以即使参加了一线的工作,可能也只是给我的从医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辞职,也是考虑了这些因素的。当时如果没有“好医生”网站的招聘,但有其它适合我的工作,我的选择还是一样的,我还是会走。 记者:非典疫情解除后,你有没有再和以前的同事聊一聊,尤其是那些参加过防非一线工作的同事?问过他们的感受和当时的生活吗? 周伟峰:我去门诊上看过他们,他们也都很忙,我只是简单的了解,可能还没有你这个记者了解的多,了解得详细,我很想有机会大家还能一起坐一坐。 记者:和他们聊这些的时候,你可能也谈到你现在的生活,你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或者说是失去了什么?因为你刚才谈到在从医和学医的11年里,没有愧对医生这个职业,是不是你认为至少在辞职之前,你是一个合格的大夫,一个好大夫? 周伟峰:我现在的生活有个变化比较明显,就是晚上不会再为科里的病人担心,不会再那样睡不踏实,梦里都会有抢救的场面,早上也能多睡一会,星期六和星期天可以多休息休息。如果说我失去了什么,可能有两个方面我的确失去了一些东西。(笑)一是工资加起来没有原来当大夫的时候多,二是没有原来那么受尊重。就在昨天晚上,还有一个病人给我打电话,说在科里找不到我了,问我到哪里去了,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病人,都快70岁了,听说我辞职了,打电话说一定要来家里看看我,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好大夫,但至少我认为我还是个敬业的大夫,一个负责任、认真的大夫。在评价一个大夫是否好的时候,我认为首先他应该是敬业的,为病人着想,为病人负责。 记者:你的家人支持你辞职吗? 周伟峰:一直到现在,我的父母都不能接受我的选择,他们还是希望我能去上医学研究生或者干一段时间的就回医院去,老老实实当医生。虽然他们也知道医生很辛苦,而且可能要面临非典那样的传染病,但他们仍然觉得医生工作稳定,有社会地位。以前我的父母是很为我自豪的,总是对亲戚朋友说:“我儿子是医生。”我爱人没有说什么,她只是相信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其实最让我觉得心里难受的,反而是一个支持我的人,他就是我的导师火树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疆内中医界名气很大。能做他的学生,我是很幸运的,火老师对我也很器重,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我辞职的事,一直到我在医院上班的最后一天,我为火老师抄完最后一张方子,我请火老师吃饭,我才在饭桌上告诉他。当时连我们科的人都不大相信我辞职的事,觉得我在开玩笑,我没有想到,火老师对我说:“走自己想走的路,我祝你成功!”(停下来,看外面,好半天才开口说话)他已经是个70岁的老人了,还是很理解我,鼓励我。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还在担心我家装天然气管道的事,在他心里,我还是他的学生,还是一个医生。 记者:你现在的身份是网站的学术推广员,与原来的医生工作相比,尽管你还是要和区内各医院打交道,但毕竟是由被动变为主动,甚至是去求人的,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作为一个思想比较成熟的年轻人,你应该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转换角色和地位,可能还是会给你带来痛苦和失落,你就没有想过再回去当医生吗?你从医院才离开了两个月,是有这个条件的。 周伟峰:(笑)的确是这样,我认识的一位本院的大夫昨天见了我还挖苦讽刺我,叫我“周经理”,“周老板”。我听了也只能付之一笑。还有,到一些医院的行政部门去,也会遇到态度很冷漠的人。如果我的心态不好,也会感觉很受伤的。也许在五六年之后,我觉得自己精力跟不上了,干这个干不动了,我还会去当医生,但我想可能性不大,我希望自己还是能在新的行业里干出成绩,比如成为职业经理人,都是我努力的方向,但我不会再轻易到医院去当医生,或者去开诊所什么的。(叹气)我太累了。 记者:最后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你有孩子了吗?如果他将来想学医,你会同意吗? 周伟峰: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如果我的孩子将来想学医,我也不会蛮横地阻止他。但我会把自己学医和从医的经历告诉他,让他明白,医生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样的,给他提些建议。 (背景调查)据记者调查,像周伟峰这样,在5—7月间辞职从事其它行业的医护人员达到了11名,这仅仅是来自首府八家三甲医院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数字。其中最高的学历是硕士,最高的职称是主治医生。有调入其它单位从事行政工作的,也有做安利产品销售的,但没有人再从事医院的工作。而在此之前,每年从首府三甲医院辞职的医护人员超过了50人。其中职称最高的为副主任医师,他们多从事与医疗行业有关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销售工作。压力大,太辛苦,风险高,成为其辞职的主要因素,非典使这些因素再次凸显。
订阅新浪体育新闻,送你皇马球票让你亲历五大球星风采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非典型肺炎防治专题 > 正文 |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