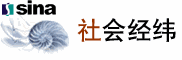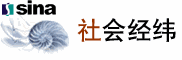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篇报道中涉及的人名和地
名做了技术处理。本文中做“自述”的包工头已经从事建
筑业近20年。他从工地上的小工干起,现在有了别墅、轿
车。用他的话说,“自己坑过人,也挨过坑”。他的“成
长史”,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些新楼倒塌、公路塌陷、
桥梁断裂的原因。
我老婆最纳闷的是,我们家哪来的那么多表亲?我说,
表亲就是路
我们这个城市只是个地级市,也就相当于北京的一个
区那么大,但里边的弯弯道道,我不告诉你,你一年半载
也不一定能钻出去,就算你们记者神通广大。
跟你这么说吧,我和我老婆结婚这么多年,她一直就
特别纳闷,我们家哪来的那么多表亲?我说,表亲多了路
好走。她不明白。
1990年我开始拉队伍自己搞建筑。那时候建筑业还不
发达,工程少,要想有活干,没关系绝对不行。最初我接
了两个单元的楼房,是人家转包了四五层才到我这儿的。
每一层都提工程款的15%,你想想我还能剩多少?那些人
有关系,给有权的人捅点钱就能得到工程,再一转手包出
去,坐在家里就能来钱。看人家挣钱那么简单,你能不好
好想想?
凭良心说,我的建筑队也不怎么样,除了我们很少的
几个人干过稍微大点的工程,其余的都是老农民,顶多在
家垒过猪圈。现在干什么?楼房!那是两码事儿。那时就
得有胆子接,实在不行,就当练练手。
一年下来,不但没挣多少钱,连原先攒的10万块钱也
填进去了。你想,工程需要垫款,各路神仙也得打点,衙
门里个别有权的都跟你伸手要钱。这是填不满的一个窟窿。
拉关系、送礼,刚来的几年,没别的,全是这个。城
市小,也有小的好处,人好找,关系好托。我有个本事,
凡是我们村十里八乡的、在城里有头有脸的,我都能拉上
亲戚。我老婆就纳闷:咱们家哪来那么多表亲?我说你不
知道,表亲就是路子——其实,不给钱你都不知道路在哪
儿。
我“上路”就靠一个“表叔”帮忙。其实他算什么表
叔,还不是钱喂出来的。我这表叔是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现在是正的了。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个副主任,平时,上班
骑辆破自行车,见谁都满脸是笑,实际上,手眼通天,本
事不小,求他的人多了。什么孩子上学,找工作,在他这
里,只要舍得花钱,没有办不成的。他过去跟我爸爸认识,
不过早就没什么交往了。
我第一次去他家,买了两条玉溪、两瓶茅台,可还是
诚惶诚恐。到人家里一看,好!客厅金碧辉煌的,29寸大
彩电、真皮沙发、木地板。一家人正在看电视。见我进来,
他老婆欠了欠身,算是让座,表叔呢,都没拿正眼瞧我。
这样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心想也别这样呀,先说这个
电视剧挺好的,我也爱看,然后再叙旧,说我爸爸让我来
看看您……表叔只是冷冷地听着,眼睛始终没离开屏幕。
我还得装得跟人家特亲,小心翼翼地说。那时候,我就感
觉自尊心像太阳底下的雪糕,一点一点地融化。我心里想,
你凭什么这样,不就是因为有权吗?就凭你一个月三四百
块钱的工资,家里能弄成这样?别装假正经,给你钱你什
么都干。
以后,每周我都要去他们家三四次,每次都不空手。
开始,他还是那样,任你怎么说,他总是不阴不阳的。我
是礼照送,话照说。不是说“物质决定意识”吗,我就用
钱塞,我就不信你总这样。后来,这位表叔也能跟我聊天
了。不过,这帮人已经是老油条了,知道你下本钱要干什
么,你不开口,他才不说”你碰到什么事啦”,但你又不
能急于求成,哪能认识没三天就要工程?这就叫“喂”。
没想到,这位表叔特黑,让我喂了整整两年。平时年
节不算,大的就有三次,他儿子结婚,我送了一套平房,
从买地皮到盖好房,一直到装修好了才送过去,花了五六
万块。第二次是他老婆调动工作,我一下送了两万。后来,
他想当个正头,要给省里送礼,我又给了两万块。
你问我亏不亏呀?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我都得从工
程上找回来。
1996年下半年,市里搞一个“安居工程”——光明新
区,市长亲自担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我想这次你得给我
使劲了吧。一期工程还没动,各路人马都虎视眈眈,托关
系,走后门,闹得乌烟瘴气。哪个包工队都有自己的本事,
甚至都能求动市委书记、市长。
一开始说这项工程招标,几乎所有的建筑队都找了市
长、市委书记,后台差不多。再说,拿人家钱不办事也不
行,干脆,抓阄吧。为体现“公平”,还制定了一系列规
定,要求以前最少干过两项工程,三级资质。我们就卡在
了资质上。最初公司注册时,我托关系弄了个三级资质,
1995年省里建筑企业大检查,没辙,我自己要求降到四级。
其实,我们连四级都不够,比皮包公司强点有限。
这回光明新村的工程要三级资质,这时候就得找”表
叔”了。还算没白养,表叔答应通融通融,最后通知我“
可以参加抓阄,但是不是能抓上,得凭运气了。”有这句
话就行。
抓阄的前一天晚上,我找了一位老先生算了一卦。你
问我怎么还信这个?开始我也不信,慢慢地我就信了。你
没看见好多大公司、大饭店都有佛龛。我那表叔家里照样
有菩萨供着。卦摊上的老先生给我算的结果是“上上卦”。
第二天,我一伸手就抓上了。工程抓到手了,自然还得感
谢人家。
过去是“酒肉穿肠过,办事不会错”,现在是“酒肉
穿肠过,伸手还要色”。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要说我是把那位“表叔”当“神”供着,那么工程中
我伺侯的就是一群鬼。建委的、质监站的、开发公司的,
除去大鬼,就是小鬼。不是有句话说他们嘛——“吃喝嫖
赌,样样都会;三晚两晚,感觉不累。”真是那样。
我们施工时,质监站的来检查,每次都是上午十一点、
下午四五点来,到工地转两圈,闲聊会儿。还没办什么事
呢,就该吃饭了。这饭死定了得你请。一顿饭二三百块,
我半年的饭费就得五六万。光吃还是好的,拿的你也受不
了,今天跟你要三四吨水泥,明天说家里装修缺点木材。
你说,我不在工程上偷工减料,我怎么办,该赚的钱你没
赚到,可不就得想点邪的歪的,砂浆标号低一点,自己进
点便宜钢筋、便宜砖。
要想工程顺利,哪炷香都得烧到了,而且现在的“鬼”
们越来越难伺候。过去,给他个三百五百的,特高兴。接
下来发展到一两千、四五千,现在呀,给钱都不行了,得
来“色”。吃喝完了,得给他们找个小姐,按摩、跳舞,
来个“特殊服务”。你没看现在我们这儿的领导都变得能
歌善舞,八成都是这么培养的。
有一次,工程保卫部的李部长找我,说,“老张,什
么时候出去玩玩”。我知道这小子又馋了,便说“随你吧,
我付账”。晚上我们几个开着车就出去了,市里的饭店他
都吃腻了,我们就去下边一个县城。别瞧是县城,照样繁
荣“娼”盛。这里有一条街,当地人称“小香港”,舞厅、
饭店一个接一个,灯火通明,不时还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
“嚎”歌声。我知道这帮家伙要什么,所以吃饭时,每人
要了一位小姐。吃饭专拣贵的吃,大闸蟹一人一个,还要
了一碗“王八汤”。平时他们花自己的一分钱也得算计算
计,吃别人的大方得不得了,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吃完饭,
还要跳舞。别看他们平时在办公室里都人模人样的,其实,
满不是那么回事。
李部长40多岁,也特好色,跳舞时把小姐搂得紧紧的,
还摸来摸去。人家自己会说,这叫“四十多岁才学坏,怀
里搂着下一代”。我坐在那儿就想,这些人都怎么啦,吃
喝玩乐,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吃喝都不叫事,这些人是要
糟踏,一顿饭一两千,花得我都心疼。你说这叫潮流吗,
过去吃喝一顿,事就办个差不多了。现在?还得有黄色的,
没有他就跟你要。
我们想赚钱,可我们也想凡事该有个规矩。这样国家
和老百姓都少损失点,个人也多落点。现在倒好,全都是
黑箱操作。就说工程款吧,工程结束都快半年了,就是拖
着不给,你就一顿一顿地请他们吃饭吧。再后来,我也不
着急了,你不是叫我花钱吗,我也别闲着,给甲方的预算
员“投点资”,工程造价抬一点,吃喝费不就都出来了。
“黑洞”不堵死,塌楼的事绝不了
我们市里有个宏远公司,1996年建了一个居民楼,还
没完工呢,主体从上到下裂了几道大缝子。也该他倒霉,
正赶上全国连续出了几起大的建筑事故,省里也查得特紧。
检查团来到市里,盯住他了。电视台跟着检查组去录像,
路过另一个小区,说顺便看看吧,结果发现比检查组原来
查到的那个工程问题更严重。一查,也是宏远公司干的。
罚款、曝光、通报,结果怎么样?一年之后,人家照样开,
工程老板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怎么赔的我还叫他怎么
挣回来。不服行吗?
干了这么多年,也不能说没遇上好人。有一个人工作
最认真,管我们最严,但也是我最佩服的,他就是质监站
的赵工。赵工50多岁,技术上很有一套。为管好工程,他
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自己也是一天两三次到工地检查,
即使发现“板凳灰”(指为偷工减料,只在砖的两头放灰,
因类似板凳而得名)你也得拆了重来。可后来,赵工遇到
了麻烦,原因就是认真碰上了官僚。
光明新村是市里的安居工程,市长亲自担任建设领导
小组组长。说起来挺重视吧,坏就坏在这上了。
1997年6月,我们承建的一个单元起主体。 下午上楼
板,这时赵工来了,一看已上去的楼板有的地方有窟窿,
问我怎么回事。其实,我早就看到了,但谁也不会傻得停
下来不用。见他问,忙说:“不知道哇。”“停了!”赵
工是绝不客气的。没办法,只得用吊车吊下来。赵工又查
看地上堆的楼板,什么窟窿的全有。更没想到的是,楼板
里的钢筋在外边露着头,我用手一掰,“喀吧”一声就断
了。这样的楼板根本没法用。再看其他工地,全一个样。
赵工心里清楚,这事跟我没关系。按规定,我们只负
责施工,材料由甲方,也就是开发公司负责。这是为了避
免我们施工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可开发公司想着肥水
不流外人田,自己成立了一个材料部。坏事就来了。市里
一家私人楼板厂靠关系挤了进来。他那里的楼板用的钢筋,
全是不合格的。这家厂子跟市里一个电焊点建立联系,把
回收的废旧钢筋一段一段焊起来卖给他。拉到我工地上的
楼板,用的就是这种钢筋,这种楼板比木板强不了哪儿去。
发现问题后,质监站一方面下令停用楼板,另一方面
要求楼板厂对自己的产品自检,结果还是不合格。可是没
多久,这家楼板厂就在小区所在法庭起诉质监站,说这是
非法执法,给厂里造成了数十万元的损失,要求赔偿。
法庭也怪,明明是质监站有理,就是不判质监站赢。
后来我才知道,楼板厂经常到这儿打官司,跟法官熟得很。
法官也有创收任务,不管谁输谁赢,都可以得诉讼费。你
来打官司,就相当于来送钱,他当然欢迎了。于是乎,今
天质监站递交的证据,晚上楼板厂就拿到手了。质监站更
怪,别人跟它打官司,它这边却跟没这回事似的。法庭通
知明天开庭,领导便临时抓一个人:“你去。”可是去的
人连怎么回事都还不知道呢。
楼板厂那边上下疏通,找到市长,市长发话,质监站
官司输得更快了。赵工呢,因为是事件的主角,被楼板厂
视为眼中钉,多次扬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果真,先是有
人跟踪,后是纪检委找他谈话,说楼板厂告他索贿。纪检
书记婉转地告诉他:“老赵,以后别自己骑车上班了,现
在车祸挺多的。”
赵工听了大怒,气得找到市长,说:“我个人无所谓。
质监站是执法单位,如果判我们输,以后真是没法干了。”
市长也不比谁糊涂,敷衍过去了事。
我看现在新闻总在说建筑质量问题,好像挺重视。市
建委主任跟我说,你们别给我塌楼就行,新闻里怎么说我
不管。可我觉得,只要是“权”和“钱”不从这里边退出
去,这些“黑洞”不堵死,塌楼的事肯定绝不了。
现在回想这二十来年,我坑过人,也挨过坑。1994年,
我弟弟考大学。家里条件虽然好一些了,但也穷怕了。我
弟弟急于摆脱影子一样的贫穷,看我能挣“大钱”,就想
报建筑方面的专业,我知道后立马叫他改了。我说:“干
我们这行的,可能说得损点,好人少。你要是有出息,就
考法律,治治那些坑人的鬼。” 柳怀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