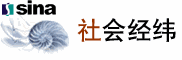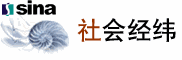他们的家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 此刻会站在这里,成
为罪犯。
1998年5月19日凌晨1时许,深圳福田区石厦工业区内
的奕达电子厂楼下忽然一声空响,一包电脑主机板从天而
降。富有“侦探”经验的护厂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里应
外合的偷盗,他们没有立即上前,而是静待贼人出现。
出现的是本厂员工,叫李朝战,当然至今无法知道他
是不是护厂员所等待的人,因为稍后事态急剧发展,使这
个结果对本案的进行已显得不为重要,但对李朝战而言,
导致他的生命的结束,就因为他不明不白地恰巧在当时在
那包物什边出现。
李朝战当即被四五名护厂队员擒获,审理当即开始。
随着审讯力度加大——拳头力度加大,李朝战供出了一个
“同案犯”。至19日上午7点,已有7名打工仔被这样顺藤
摸瓜牵出。审讯日以继夜,上午8时,7人全部被押上一辆
中巴,来到同属于老板的另一工厂仓库里。这时候,工厂
老板、香港人孙世强尚未露面,但一切分明都在他的遥控
掌握之中。数十名内地籍工厂主管、护卫员蜂拥而至,轮
番而且尽其所能地开始这不同寻常的表演。 首先他们将7
名打工仔分开,分头审讯,防止7人通气,其次令这7人全
部脱掉鞋子、衬衣,并且跪在地上。工厂主管钟志良在审
讯李朝战时,声音越吼越大,最后,不得不用一黑色手电
筒来表达这种气愤,其他护厂队员为了给主管解气,于是
立即上前展开一番拳脚语言。开始还比较克制,后来,他
们拿起了手电筒、方木棒、钢管,打手部、背部、脚部。
就像人类最初拿起工具完成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一样,他们
这群人拿起了工具,也完成了一次相反方向的转变。
第一轮打完之后, 主管们让7个打工仔自己用纸笔写
坦白书,写偷盗经过,写检讨,写完之后主管似发现不合
他们心意,又展开第二轮殴打,就这样打了写,写了打。
但 4名主管和10多个护厂员的轮流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
至中午时分粗大的方木棒竟被用力过猛打断了,至下午,
7名打工仔都已奄奄一息。 据沙头派出所公安人员事后了
解到,当时一名打工仔被一名主管飞起一脚踢昏过去,在
场其他人马上用冷水泼醒,然后再打, 直到下午6时许,
这名不省人事的打工仔才被抬出去。从上午到中午、下午,
这 7名打工仔滴水未进,而打人者却不乏悠然。打人者之
一梁卓兴在派出所承认,“上午他在仓库内参与殴打,中
午11点半出来吃饭,下午2点多又回到仓库内打人,1小时
后出来,4点多又进去,5点半出来吃饭。”这天,他在工
作间隙,闲着没事时就打人去了。另一名主打者钟志良说,
之所以会把人打死,就因为他们时不时地出门休息、处理
其他事,回来再打时没有掌握好被打者的伤势情况。
当然以上的打只是手段,为了要个结果,好向一直在
家里遥控的老板汇报,后面的打可就更接近本质,动起真
格的了,因为老板来,老板也打开了,他们这时就不光是
要打,还要打得漂亮。不光是用体力,还有想像力,要打
得不留痕迹,打得你心服口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被打
者没有叫唤的力气,直到李朝战口中只有出的气,没有进
的气。
事后,20日下午福田公安局老韩到达现场,发现,当
时现场虽然已经清洗过,但仍可见无数蚂蚁在疯狂搬运剩
余血迹。可见当时场面之血腥。
这里尚需交待的是,19日晚9时许, 沙头派出所干警
曾接到110电话有群众报案,火速赶到工厂, 却被工厂主
管挡了驾,他们声言平安无事。20日凌晨时分,奕达厂护
卫主动向当地治保会报案,称厂里有人自杀。这时沙头派
出所值班领导与两个干警赶到现场,汤副所长发现现场可
疑,死者仰面朝天,尸体很直,裤腰带解开,光着脚,更
引起他警觉的是死者脚部分伸在一个推土机的铲斗里。汤
副所长立即叫来福田公安局法医验尸,这才发现死者遍体
鳞伤,但没有跳楼自杀的致命伤处,遂把工厂有关人员带
回问讯。
死者正是李朝战。李朝战被打死后,香港老板立即打
发走正在接洽的客商,召来几名工厂主管及护厂员,商定
对策,最后决定伪造假现场。
他们的设计思路是,李朝战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
写检讨书,写着写着,就畏罪自杀,跳楼身亡。他们在二
楼的物料仓库内放置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张纸,一支笔,
最后是4名护厂员打开一扇窗户, 将李的尸体抱到窗口放
下去。
而对另外六名被打者,护卫队员人性觉醒先给他们每
人一份炒米粉,然后恐吓:“你们偷的东西最后卖给了香
港黑社会,现引出麻烦,他们为了杀人灭口,现要找你们
算帐,我让你们走,马上离开深圳,不要再回头。”
5月20日凌晨起,13名参与非法拘禁、 殴打事件的犯
罪嫌疑人分别被沙头派出所收容审查。
6月3日福田区召开公开逮捕大会,宣布对上述犯罪嫌
疑人逮捕归案。
打人的和被打的一样可怜
那天在福田区大会堂门口高高的台阶上,古铜色的囚
服、十三颗低垂的头颅、两边威严的武警以及对准他们的
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久违了的高音喇叭都让人感到严肃、
紧张,透不过一丝气来。
我久久地凝视他们,我想他们远在家乡的父母妻儿此
刻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在深圳做事的儿子、丈夫、父亲
此刻会站在这里,接受这样的仪式。十几天前,在父母妻
儿的眼中,他们是“有出息的”,他们同样来自于一个个
僻远的乡村,他们也正艰难行走在通向小康理想的小径上,
他们同样地付出汗水、心血(当然更多的是人格、道义),
他们同样用大量的剩余价值去换取那一点点的劳动力成本
……
但他们杀了人!
我把照相机的镜头一次次地对准他们,希望能捕捉到
一些流露于眼神的凶光,然而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悲戚、
惊恐、抖颤的脸庞,有的甚至还有没褪去的大男孩子稚气
……
他们原本属于打工者中的一员。
是什么使他们从一个队列站到了另一个队列?我想知
道当时是什么力量鼓舞他们、使他们一次次地握紧拳头、
挥起铁棒,重重地打向一个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他们同类身
上。
可以肯定,将一个健壮青年置于死地决非“举手之劳”
“瞬间一念”,公安机关的调查证明其中有漫长达24小时
的肉体折磨。行为上的实施已属不易,而难度,我想更在
于对自己内心防线的突破。“人命关天”、“生命属于个
人只有一次”,我相信这些出身于普通人家的子弟对这些
观念是深入骨髓的。可以相信,他们从始至终是没有致人
于死地的愿望,但又是什么力量牵引着,使他们向这个目
标一步步靠近的呢?被打者之一苟茂青之前曾被打昏过去,
可用水浇醒之后又继续打,可以想见如果李朝战能够再次
被水浇活,他的刑讯也不会到此结束。结果似乎早就注定
是唯一的。
在看守所,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还全处于“懵”了的
状态,他们好像还不知道为何会被带到这里,怎么打死了
人。我问他们,“你从内心里憎恨李朝战吗?”“不恨。”
“那为何要下毒手?”“……”“如果你们要不打呢?”
“老板让打,给他打工,就要打。”“你们知道打人犯法
吗?”“知道。”“知道,为什么还打?”“……”正如
他们现在“懵”了不知怎么打死了人一样,当时他们也可
能一样不知怎么会不打。给老板打工,打人是工作,打工
就要打工,打人即是打工。
我曾问另一个工厂的保安,问他对此怎么看,他说在
那种情况下,不打是不可能的,不打即使老板不炒你鱿鱼,
你也没法混下去。在工厂当护厂员就要有点威风才能镇住
大家的,这威风一半是靠打出来的,一半是靠势力树起来
的。同事都打,你不打,你会被孤立,在工厂里如果一个
保安是孤立的,他无论如何是做不下去的,即使同事不欺
负你,那打工仔也会看在眼中,找机会收拾你敌我矛盾如
此严峻!
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磁场,当这一枚枚小磁放
进去之后,它们就无法阻挡地具有某种极性?对于这一个
个打工仔来说,当他们置身于那样强势的环境之中,他们
也无法摆脱他们命运中被赋予的这种或那种、打或被打的
角色的。
从奕达厂老板孙世强的口气中我不仅看到了这个场,
而且我分明感到了这个巨大磁场的能量。孙世强在刑讯时
说:“你说不说,想跟我斗,我用一卡车货20万就可以搞
定你们全家。”当然他的另一半话,早已深入打工仔骨髓
里,好好干,听我的话,我给你们工作,给你们钱。
当金钱转化为一种精神能量,或者说当精神力量可以
用金钱去衡量、去发动、去补充、去放大时,能与之相敌
的还有什么?
采访中我曾反复地想,什么才能阻止这次人命事件的
发生。许多传媒同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法,指出他们的行
为缘于对法律的无知。这样来解释每个个人是合理的,便
对于决定这么一群人一致行为的集体意识是无法圆满的。
可以假设如果其中某人明白了这样做是违法的,那他只会
终止个人违法行为,使他这一份违法力量变成零,但这并
不能导致整个事件的终止,事实上能够阻止事件继续下去
的,必须有一种能和这种力量相抗衡的内部力量出现,来
抵消、减弱以至于合力为零。这种力量可能是对弱者的同
情、对残暴的愤怒、对正义的维护……然而我却悲伤地看
到,在事件演进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力量从未出现。在整
个漫长达24小时的非人折磨中,始终没有人出来阻止,或
者表示出异义——这是一种失衡,一种导致必然结果的前
提性失衡!
在采访中,这个结论又一次得到侧面证实。我问过不
下二十名这个工厂里的打工仔,你们对保安员印象如何?
普遍敌视。那你愿不愿当保安?不愿。当我把问题的顺序
调个个再问其他人时,其答案正好相反,他们都愿意当保
安,保安不用站流水线,工资又高。当一个人对他敌视的
工作充满向往,这种矛盾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扭曲,而这种
扭曲必然带来的是人格的变形,道义的丧失。而在一个道
义沦丧的群体里,还会为此类事件感到意外吗?
我只是感到打人的和被打的一样可怜。
蔡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