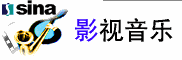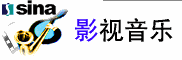近日在贵报的一期中,有幸看到了邵牧君先生写的《
贺岁片之管见》一文。文中提到“看电影不就是消闲找乐
吗?难道非要念念不忘、永留脑际才算是物有所值吗?”
看完轻描淡写的这段话,我如同五雷轰顶,什么时候看电
影竟成了“就是消闲找乐”?
类似《不见不散》这样的商业因素较多的片子无疑是
电影的一种存在方式。但它不是电影的全部。电影是什么,
对于邵先生这样的电影史大家来说,简直是一个极幼稚的
问题,可是“看电影不就是消闲找乐吗?”又说得多么绝
对,作为评论界的资深前辈、邵先生绝不会无端他说出不
负责任的话,或许他只是想借用这样一种绝对话的语气来
表达一种对中国电影业萎靡不振的优虑与不满的情绪?他
只是想为中国的电影能尽快走上商业化道路助助威?但无
论我怎样加以合理化的解释。白纸黑字总让人心中不快。
问题在于,话不应该是这样说的。
《不见不散》充其量可算作一本畅销的流行小说。若
按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从中还能看出些小农经济的特点:
缺乏眼光,无想像力,在整体组织上和技术上都有致命的
弱点。这就无怪乎有人说它肤浅;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
记的是,世上还有诸如米兰-昆德拉写的作品, 如同电影
中的《红》《白》《蓝》。
诚然,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是邵先生的一贯主张。可
能到了3000年,“电影是第七艺术”这样的提法就不会再
有了吧?因为工业化大生产与艺术个性的共存问题,起码
当前的人类还无法妥善地解决,可是看电影就为了找个乐,
给观众逗笑了就是成功的电影,倒让我想起了电影的雏形
阶段。电影在一开始还真就是这个目的。是不是世纪末情
结的原因,邵先生也开始怀旧起来了。那么电影后来怎么
就度过了一段不应该有的爱森斯但、安东尼奥尼、伯格曼、
黑泽明、基耶斯洛夫斯基阶段,才好不容易找准方向,回
到了《不见不散》呢?
邵先生强调指出,应加强电影的可看性。这一点我举
双手赞成。本来嘛,电影是一问视听艺术,起码得要好看
好听才行。而现代的电影作为被现代化商业社会所容纳的
一部分,加入一些商业因素本也无可厚非,但要留神,过
犹不及。正像邵先生说的“讨观众的喜欢”,一个“讨”
字,态度全出来了。
其实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并不
是可望而不可及。《甜蜜蜜》不就在我们面前摆着吗?纵
哪一部不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既有哀怨动人的《失乐
园》,又有清新隽永的《谈谈情,跳跳舞》,或者是《情
书》《燕尾蝶》《鳗鱼》《不夜城》,有言情,有揭露社
会问题,有暴力,风格各异。我并不是说中国也要拍艳情
片、暴力片,只是想说明各种风格和题村的影片只要做得
好,都会在市场中找到它的位置,为何非要把目光投向“
贺岁片”,可国内当前的情况偏偏是除了贺岁性质的具有
喜剧色彩的片子能向观众讨个赏钱外,还有哪部片子能赚
钱?这其中的问题究竟出在谁身上?看着日本电影、伊朗
电影、巴西电影等佳片不断,中国的电影人是不是该好好
反省一下了?
我认为还是当前电影创作的整体心态过于浮躁,只盯
着眼前小利,不能踏踏实实地真做点儿事儿。有人会说,
你总得对投资人负责吧,搞艺术片,赔得一塌糊涂,那人
民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好,《猜火车》赚不赚钱?
《一脱到底》赚不赚钱?它们对没对得起投资人?有人又
说,这种片子在中国肯定不赚钱,连审查都通不过。那是
因为国情与文化的差异,不符合中国的口味,那么既可通
过审查,又能被国人接受,而且有相当品位的片子可不可
能有?类如上面说到的《甜蜜蜜》。邵先生说拍电影的第
一条件是金钱,这只是物质条件而已,有一亿人民币就一
定能出部好影片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第一条件,那就是
电影创作人的素质条件,有多少本事才能出多少东西。
说到这儿,想起了上个月一次在火车上与一位乘务员
闲聊。我问她最近哪部片子觉得还不错。她回答说由于工
作原因,再加上实在没什么吸引人的片子,她已经两三年
没进过电影院了。她想了一下接着说,她前两天看了一部
日本电影《燕尾蝶》,觉得相当棒,看一遍还不过瘾。当
时我很惊讶,我以为当前的年轻人只会喜欢《还珠格格》
《泰坦尼克号》和《不见不散》,喜欢时尚的东西,不会
再用心接受和体验什么,结果我错了。谁都不要低估观众
的欣赏水平,谁都别把观众当傻子耍。春节晚会办得怎么
样?《雍正王朝》拍得好不好?《不见不散》究竟是怎么
样的一部电影?观众心里清楚得很。
说到底就是一个心态问题。拍电影的认认真真地拍,
看电影的认认真真地看。未必搞大片、贺岁片就是好事儿。
就像足球,不一定狂攻猛打就能赢球,像大连万达队那样
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也一样赢球,关键还在于本身的实力
和素质,否则再怎么析腾,也只是虚张声势、最后还得原
形毕露。事儿虽然不是一码子事儿,但道理是相通的。至
于邵先生的“看电影找乐”论,恐怕也只是一种无奈之辞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