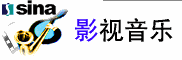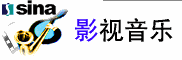听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昨晚在世纪剧院演奏郭文景的
笛子协奏曲《愁空山》和西贝柳斯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
忽然想起《关公战秦琼》的相声段子。
郭文景之于西贝柳斯,比起关公之于秦琼在空间距离
上可能还大些,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时间顺序上却
有一点可以肯定,西贝柳斯绝不可能作出郭文景式的现代
作品,尽管他对芬兰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影响巨大;而郭
文景却是具有可以作出西贝柳斯式的作品的天才,因为在
《愁空山》中,我们可以听出他驾驭音程关系、和声关系
的能力已无可指摘。
问题在于,郭文景毕竟像西贝柳斯一样不能作出对方
那样的作品。我们不说先锋派、前卫派的不屑,至少在音
乐的和声、配器学等发展到极致的今天,在离我们最近的
晚期浪漫主义和前卫派之间,出现着一个巨大的作品创作
空白和断层,更不要说推至古典的贝多芬、浪漫的门德尔
松。这不能不说是音乐的一个即在的悲哀。
拿流派相比也许多少有些“关公与秦琼”式的滑稽,
但是如果真的能够让关、秦二人在一起较量一番,肯定会
产生一个“谁是更完美的英雄”的结论。
同是三个乐章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愁空山》,
让人听来似乎前者更具有完美无瑕的线性乐感,是因为它
代表着人类更加理想化的美感共性,因此,它流畅、顺达,
其突出特点是无可厚非的旋律性。而《愁空山》则急不可
待地张扬着强烈的个人理念和主观理想,给人一种不用跳
来蹦去的断了层面的意识流来呈现,就不足以推动浮躁不
稳的思绪上的多米诺骨牌的迫切,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旋律,
但这旋律至少是点状的、稍纵即逝的。人们会解释,这种
前卫的、先锋的感觉和我们快节奏、无序的忙碌的现实生
活多少相似。但这是不是有些自然主义呢?沉溺于自然主
义是前卫、先锋派拂之不去的一个影子。如果这是一种流
派,我们还说什么?
作曲家的主观意志固然是音乐之“源”,但是音乐得
让人听得懂,这是“流”,合起来才是“源流”。昨晚记
者采访了乐团首席克里斯·托瓦迪森,问他:“你是否喜
欢《愁空山》?”“你能理解它吗?”“你如何解释它?”
拉了许多遍这个曲目的托瓦迪森说:“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作品。我们演奏从16世纪到现代的许多作品,拉这首
曲目没什么困难。观众会慢慢理解的”——答未及问。
作曲家郭文景认为这个比国内任何乐团都能诠释得好
的乐团首席没有说出他对这个曲目的理解是什么。看来,
他也没有真的读得懂它。 记者白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