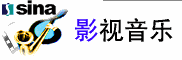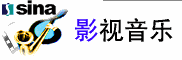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特别是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
电视记者、电视主持人,这要归功于一个名字——《东方
时空》。
从迈进新华社的大门开始记者生涯以来的14年里,绝
大多数时间,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编辑。我并没有
指望过有一天会成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像有些朋友所说
是一个“名记者”、一个“大腕”记者、一个名主持人。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水均益”这样一个很怪的姓所带出
的一个名字,能够被人们所熟悉。
转折的一天
1993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准备睡午觉。突然, 盖
晨光对我说:“水哥儿们,我想起一件事,昨天《焦点时
刻》的制片人张海潮跟我说了一个想法。”
盖晨光露出了一种神秘、庄重的表情。他说:
“《焦点时刻》节目组的制片人张海潮,希望由一位
当过记者、对国际形势又比较了解的人,来当国际题材节
目的记者主持人,我已经向海潮很郑重地推荐了你。我说
小水没有问题,他当过很多年记者,而且在中东也干过。
情况非常了解,对国际形势没得说。”
我从用三张椅子拼凑而成的“小床”上坐了起来,一
时有点茫然,问道:
“我?我行吗?”
“如果你能熬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觉得你肯定能行。
而且这对你来讲可能会意味着很重大的变化。你记住我的
话:有一天你会成为名人,也许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
现你的脑袋上会有一个光环。”
直到今天,我总也不能忘记那个中午的谈话。
普通话露怯
1993年5月,我正式“触电”。 我们开始准备一个关
于中东和平谈判问题的节目。这是我初次上镜,我们请来
两位专家,准备在演播室里对他们二位进行访谈。
虽然我已经参与过两期节目的编辑工作,知道节目主
要形式就是主持人与专家一问一答。但是真的落到我自己
头上,心里也没有底。晚上在家里,我开始撰写需要我单
独对着镜头说的那两段话——一段开场白,一段结束语。
我写了又写,大概写了四五遍,直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为止。
然后一个人在家里模仿电视播音员说话的那种语气,琢磨
说话音量应该多大,等等。
老实说,我对自己的普通话没有任何自信。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兰州人,虽然说经过百般努力,我的普通话和
我的同乡们相比应该算是过关了,但是兰州方言中前后鼻
音没有区分,这使我经常在正宗普通话环境中“露怯”。
记得中学时第一次上语文课,老师点到我,让我念一篇课
文,内容就是《东方红》歌曲的歌词。那时候我一句普通
话也不会说。我硬着头皮,站起来,怯怯地念道:“敦方
混,太阳深,准国出了个毛泽吨(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等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只记得我的
周围一片狂笑。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直到现在,我时常
会收到观众的来信,指出我在某一个节目中的某一个发音
不准。普通话比我过硬的父亲,也会不时地在电话中婉转
地提醒我某一个字应该如何如何发音。我自己也非常渴望
我能像我的中学校友、现在《新闻联播》担任播音员的李
修平一样说话。无奈,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这一切
似乎是太难了,也太晚了一点。
第一次“触电”
第二天上午10点,在一种稀里糊涂、基本上没有什么
自信的状态下,我来到了演播室。走到门口,有人告诉我
说,你进去吧。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小时候被推进照相馆照
相那样。平生第一次坐在电视主持人的讲台前,我感到呼
吸频率加快,好像周围的氧气不够。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
紧张。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得也特别多:外面切换导
演台旁边的人会不会笑话呀? 我身边的两位专家会不会笑
话我呀?等等,等等。
灯光一亮,盖晨光在外面一声令下:开始。我对着正
前方开始了我的开场白。一句话之后,我的脑子里猛然间
一片空白。我已然忘了我应该说什么,或者说,我在说什
么。面前那个玻璃片的镜头使我感到极不自然,我的眼睛
不自觉地在躲避它。不到一半我又忘词了。外面的人( 估
计是导播)说,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遍。重来。 灯光
一亮,我又开始了。但是,还是只说到一半,又忘了。每
到这时,我的嘴里就在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那一个上午,仅仅为了一段开场白我一共录了七八遍,有
一遍刚说了一个“观众朋友”,就“你、你、你”了半天,
也没把“好”说出来。最后,总算连滚带爬地通过了。
我就这样走进了《东方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