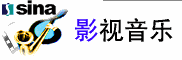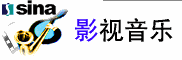德国《明星》杂志记者:斯皮尔伯格先生,您的联邦
十字勋章放在哪里?
斯皮尔伯格(简称斯):在家里,与所有对我来说特别
重要的奖章放在一起。联邦十字勋章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
的一个。
记者:这枚勋章是因您在4年前创建的肖阿基金会---
大屠杀基金会---的出色工作而授予的。
斯:授勋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在54年前,我也可能在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也可能在大屠杀中遇难。转眼间我突
然得到了德国的最高勋章。这表明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
如今德国已成为一个人们对我表示尊敬而不是要杀害我的
地方。
记者: 目前您的肖阿基金会已经采访了49468名大屠
杀的幸存者,并将他们的证词制成了录像。因此您创造了
世界上最大的此类多媒体档案馆。细看所有这些采访要用
13年零27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基金会是您最重要的项目
呢?
斯:这是我最重要的业务。它关系到一个真正的拯救
行动。因为幸存者早晚会离开我们。而这个档案馆将同全
球5个纪念馆联网。
记者:十年来德国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在柏林建一个
大屠杀纪念碑。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纪念碑吗?
斯:是的,应该建点什么。至于是建纪念碑、博物馆、
方尖塔还是象征性的艺术品,这应该完全由德国人自己来
决定。它应真正成为德国人的纪念场所,是出自德国人民
内心的愿望。如果我能为此做点什么,我觉得太棒了。如
果柏林的纪念场所能被宣布为肖阿基金会的第六个档案馆,
那我感到非常高兴。
记者:参观者可以在这个纪念场所了解到什么呢?
斯:应当有许多装有电视屏幕的沉思室,人们可以通
过播放录像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幸存者的讲述。首先也许是
德国幸存者的讲述。然后我想应该有一些“相互作用”的
房间,在这些房间里人们可以通过电脑查找资料,可以通
过档案和幸存者的证词来研究某个课题。它不一定非得是
巨型建筑。它应当是一个思考的地方----思考昨天发生的
事情、今天人们的感觉和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它应当是
一个使人们陷入沉思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受到幸存者
的言词的激励。
记者:但是好多人根本不想听我们有罪的过去----
斯:因此,这对希望了解有罪的过去的人来说更加重
要。所有的国家都有必要使人们了解那时发生的事情。这
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一个有关仇恨和非人性的经验教
训。看看波黑吧,看看卢旺达,看看所有那些发生种族屠
杀的地方。我们出生时是没有仇恨的。人们并非天生就有
仇恨,但可以被教育成满怀仇恨。重要的是教育:对教师
的教育,对父母的教育,然后对孩子的教育。幸存者们可
以成为老师。
记者:您希望----如果不是通过像《辛德勒的名单》
这样的电影----如何达到教育父母和孩子的目的呢?
斯:我们打算到学校去。我们想为此制定一个教学计
划,即制定一个关于怎样在课堂上讨论侵犯人权问题的教
学大纲。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大屠杀,而且也关系到奴隶制、
对同性恋使用暴力或灭绝印第安人。如果所有这些都能在
我们的学校里讲授的话,那么我们的孩子肯定可以学到他
们怎样与各种人交往的很多知识。这关系到教育孩子学会
宽容。
记者:您有十几名亲戚在大屠杀中丧生。作为犹太人,
您是否觉得很难同德国人交谈和与德国人打交道?
斯:我只是做了一些反对纳粹的事。您知道,德国人
喜欢把自己孤立在一个羞愧、遗憾和负罪的真空里。他们
应当看看四周:其他民族也有做得太过分,置恶于善之上
的地方。
记得: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大屠杀的?
斯: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有一
些老人来到辛辛那提我祖母的家里,他们是来学英语的。
其中有一个人试图教我数字,他给我看他前臂上的数字:
“这是3,这是7,现在我给你看一个小把戏:这是一个6---
然后他把胳膊翻过来--现在是一个9。” 我就是这样学会
数字的。后来我才得知,这些人是匈牙利和波兰裔犹太人,
大屠杀的幸存者。那些数字是他们在集中营里被刺上的。
记者:您的母亲利厄曾经说,在您家里犹太人并非是
常谈的话题。那您是怎么得知您是犹太人的?
斯:在我的朋友们称我是“肮脏的犹太人”时,我知
道自己是犹太人。有几个人打了我的脸。在家里我们极少
谈犹太人。有时我正统的祖父母来看望我们,我们就把大
虾藏到床下,在冰箱里放一些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
记者:邻居对您的家庭反应如何?
斯:不管我们搬到哪里,我们都是唯一的犹太人。在
新泽西,圣诞节的时候,整个市区披上节日的盛装,只有
我们的房子没有装饰。 那时我6岁,我问父亲我们能否至
少在门上挂一个红灯泡。他拒绝了,他说:“那看上去像
是妓院!”现在他82岁了,在肖阿基金会工作。他是位计
算机专家。
记者:您曾经想做个犹太教徒吗?
斯:当我父母把我送到犹太人中心时,我抗拒说:我
要做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受人喜欢和不被仇视的人!有一
次我甚至用一块白亚麻布把自己裹起来,把双手染红,在
白布上画一道流血的伤口。然后让彩灯照着我,我张开胳
膊站在门前,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停下车给我照相。
我在孩童时代就很想使自己同化。
记者:您曾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羞耻么?
斯:是的。当时我简直不能理解。
记者:您什么时候接受您是犹太人这个事实的?
斯:到我能够接受这一事实肯定花费了很多时间。也
许就像我制作的电影里一样,因为在拍摄期间我总是不断
地找出新的我。电影拍完了,我也就消失了,必须重新去
寻找。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它实际上开始于1985年
我第一个孩子马科斯出世的时候。现在我们每逢星期五就
点起蜡烛,去附近漂亮的犹太教堂做安息日礼拜。
记者:您的祖先来自奥地利和马克兰。您寻过根吗?
斯:在奥地利找过,在乌克兰没有。我只能把我的祖
先追溯到为斯皮尔伯格的一位男爵工作的农民身上。那大
概是1835年。他们采用了主人的名字,这在那时是常有的
事。我是在俄语和依地语环境中长大的。
记者:如今您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导演,并被认为是
最知名的犹太文化的代表。
斯:这令我自豪。
记者:您是在为宽容而斗争吗?
斯:也许是。但我有生以来几乎没有为什么斗争过。
我以前也从未信仰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