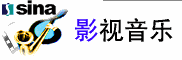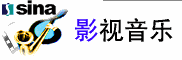“在某一天的下午,突然起了风。”
“起风了,好好活下去。”
久木和凛子踏上了殉情的不归之旅,小说《失乐园》
却用这样缥缈诗化的语言,来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读来
令人血脉贲张,热泪沾襟。这是电影《失乐园》怎么都难
企及的表达。
“法国红葡萄酒,甘甜醇郁,使人感觉到有着好几百
年历史的,欧洲的丰饶和传统,以及逸乐的情调。”久木
在上好的法国葡萄酒里,虔诚地掺进银白色的氰化钠粉末
之后,小说《失乐园》以“火焰般通红的液体”和“玫瑰
色的死”等词语,来探讨死亡主题,提升对爱情的思考。
这显然也是电影《失乐园》不能企及的表达。
在小说《失乐园》中,梦幻与现实,心灵与肉体,欢
愉与痛楚相互交织;奇妙隐秘的心理活动,与错综复杂的
情感纠葛,溶入日本独有的四时佳景。这当中,除了冬瀑、
春阴、空蝉、花落之类的意象,在电影《失乐园》中尚有
迹可觅之外,其余的精神都无处可寻了。
于是我们只窥视到了一次普普通通的不伦之恋,一次
比较流行的婚外情,一次具有日本特色的造爱。而当我们
看到男女主人公,久木和凛子双双自杀殉情的时候,我们
这些肤浅的粗鲁的观众,竟然愚蠢地觉得他们的反抗有些
过分,举动有些造作,死得有些夸张。作为小说《失乐园》
的读者,我们能够领悟,男欢女爱登峰造极之时,那种君
临天下一览众山的豪迈气概;更加能够领悟,从性爱的绝
岭雄峰,骤然跌落死亡的万丈深渊之瞬,那种史无前例无
以复加的极乐体验。而作为电影《失乐园》的观众,我们
没有这份聪明劲。
我们只能说,“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对电影来讲是
一件极困难的事情。一些聪明的电影导演,干脆采用独白
和旁白等“广播”手段,来处理那些精致得无法改编又无
法舍弃的文字。比如阿诺编导杜拉斯的《情人》,一开幕
就是一大段旁白:“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开场
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
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
那时候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其
它由小说名著改编的电影,如《日瓦戈医生》、《走出非
洲》、《教父》、《与狼共舞》等,无不采用了旁白手法。
另外一些导演,则干脆以“不忠于”原著的手法来改编电
影,并且选的都不是名著。比如张艺谋,他几乎所有的影
片都由小说改编而成,但他都没有忠于原著。他总是从影
像与声音的角度,为他要表达的小说寻找一种替代物。比
如《红高粱》里的祭神仪式,《菊豆》里的染坊,《大红
灯笼高高挂》里的开灯仪式,《秋菊打官司》里的红辣椒,
《活着》里的皮影戏,等等。
阿兰-罗伯-格里耶就曾经站在他的宗师爱森斯坦一边,
坚定地指明:“当人们把一部伟大的小说搬上银幕时,这
部小说将遭到完全的破坏,一般来说,改编出来的影片总
是荒唐可笑的。”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因为一个画面是不能忠实于一段文字的,小说与电影是两
种不同的载体。
读过小说《失乐园》的读者,如果又看了电影《失乐
园》,那么就有两个《失乐园》:一个是弃医从文的渡边
淳一的《失乐园》,一个是当红影星役所广司的《失乐园》
也有两个久木,两个凛子,两个恋爱。也有两个死,一个
崇高,一个莽撞。 盖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