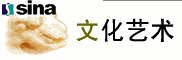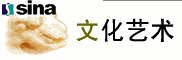花瓣总是和美好和关怀和爱和怀念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冰心先生的爱女吴青专门选择了一捧殷红的玫瑰花瓣,
摆放在客厅当中微笑着的母亲照片前。这平和的场景让人
联想起冰心先生曾说过的话:“玫瑰既艳丽又有清香的味
道,但玫瑰的刺正表现了它的风骨。”
吴青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她说,母亲最后的日子是
安详的。今年2月5日,她开始发烧。退烧后虽有清醒的意
识,但她的话少,经常自言自语---毕竟已99岁了。2月14
日和24日,北京医院分别报了两次病危。 2月14日那天,
我就坐在她床边,轻声唱起《平安夜》———这是母亲在
我们儿时经常和我们一起唱的歌。我觉得她当时有反应,
甚至跟我哼了一段。
冰心先生从1994年2月开始就住在北京医院, 之后再
也没有回过民族大学教工宿舍她的住所。在吴青的印象里,
母亲是很坚强的,也是很有事业心的。1980年她得了脑血
栓后,不能够拿笔写字,她就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因
为她觉得自己应该再做一些事。等她后来好一些了,就又
开始练习毛笔字,一天一篇。她那时写了散文《生命从80
岁开始》,让好多耄耋老人激动不已。
冰心一生倡导真善美;她提倡民主、科学与正义;她
爱祖国,爱这个命途多舛的民族;她热爱海,她有着母亲
博大的心怀;她的爱是世界的,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她
爱世界上所有的真善美。冰心先生十分达观,她在1990年
10月14日曾立下遗嘱:“我如果已经昏迷,千万不要抢救,
请医生打一针安定针,让我安静地死去;遗体交北京医院
解剖;骨灰放在文藻的骨灰盒内,一月撒在通海的河内;
墙上的字和书柜上的书,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身后如有
稿费寄来,都捐给现代文学馆;工具书可以捐给民进图书
馆。”
谈话间冰心家的电话响个不停,一位冰心生前的年轻
的“小朋友”说,从今早开始,电话平均每分钟一个,其
中有记者、学者和关心热爱着她的国内国外相识与不相识
的朋友、读者。她家中客厅里放有两个玫瑰花篮,一个上
写“冰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个是冰心家乡福建冰心
研究会冰心文学馆献来的。花篮的背景是墙上的一幅木制
对联:“是应终未是;闲得且须闲”,另有“世事沧桑心
事空”的条幅。
这些都是冰心先生生前最喜欢的。吴青说,母亲爱诗、
书、画,在她最后住院期间,每次去,母女俩总在一起背
唐诗宋词,比如《满江红》、比如《水调歌头》,及吴青
童年时的儿歌。吴青说,我小时候,萧乾叔叔是我们家的
常客,我们总把原名萧秉乾的萧乾叔叔叫作“饼干”叔叔。
吴青说,谈起这些儿时趣事,我母亲总是笑个不住。她平
常最爱吃冰激凌、猕猴桃,但病重住院期间,这些都不能
吃了。今年春节时,她也没能吃一个饺子或一个元宵。她
一直昏迷着。
冰心先生的卧室整洁温馨。屋中有两张单人床,一个
大写字台。柜子上有喜爱她的人送的冰心塑像,旁边是一
盆青绿的富贵竹和一盆美丽的水仙花。写字台上摆有香港
回归一周年时她获得的奖项———第一届中华文学艺术家
金龙奖-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颁赠。 写字台上还
摆着诸多文学奖牌和家乡人为老人95岁大寿送的金盘。她
的书柜还留有她的痕迹———有许多外国作品,当代作家
的作品和她自己的书。
冰心家里来自武汉的20岁的保姆小蓉说,冰心老人住
院期间,她去医院送冰心老人的生活用品。老人精神好时,
就和她亲切说笑闲谈,让她觉得90多岁的老人好像是个孩
子。小蓉说,她一笑,很好看。所以有时小蓉就会请求说,
奶奶,您笑笑吧!冰心就笑了。护士们也都很爱她,会找
机会和她说话,问她外语:“冰心先生,‘早晨好’怎么
说?”她会认真地用地道的语音教她“Good morning。”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是读着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
《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小桔灯》和她的诗
辑《繁星》、《春水》长大的。今早,北京外国语学院第
一天开课,吴青在给英语系9701班上课之前,说起冰心生
前常告诉她的话:“无论什么事发生,生活仍将继续。”
班上的两位女生说,她们在吴青的课上曾多次感受到冰心
对祖国、对人民、对世界、对全人类的爱。去年元旦,97
01班全体学生曾送给冰心先生一张精致的贺卡,表达爱和
关怀。
人们正把冰心所给予过他们的爱与关怀返还给她。
记者徐虹实习生鲁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