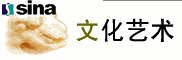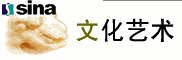半个世纪即将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一代随共和
国脚步走过来的学人,有责任对风雨50年的文学经验作
一番回眸、逼视、反省和拷问,目的是更好的前瞻和行进。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过“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
“八、九十年代文学”及“女性文学”等几次小型学术对
话,都是围绕“共和国文学50年”的总题目。
就当代文学50年而言,一般的分期是17年、“文
革”、新时期三大时间段落,且已约定俗成。然而也不妨
取另一个视角,即衡量当代文学有三个时间尺度:“历史
时间”尺度,以千年计,看当代文学在中华文学通史中的
地位;“命运时间”尺度,以百年计,看当代文学在本世
纪的艰难历程;“变革时间”尺度,大致以20年计,看
当代文学风雨路上的过渡与转型。作家作品是否有力度、
深度、厚度,需要和这三个时间尺度联系起来考察。
1949—1999年的文学值得认真总结。回望来
路,如果真诚面对逝去的岁月,那么,我们有过解放了的
人们走向新生活时发自内心的“早春情调”;我们为世人
提供了“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形象体系(同时保留了
时代某些变态的弱点);我们又力图把文学变成一统的、
体制化的东西————其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失误和陷落。
70年代末以来思想与艺术的解放运动,重新使文学从一
元走向多元,从一统走向多样,开始步入“两个自由”—
——艺术上自由发展、学术上自由讨论的境地。
“共和国文学5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合理延
伸,是百年文学的必然走向。这50年为我们提出了十分
丰富、复杂的可探讨的话题。我以为主要有:文学理论与
改革的演进;当代文学的自律与他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及其得失;文学的社会职能及精
神投向;新人形象的塑造;叙事与抒情的变奏;“双百方
针”的曲折与起伏;文学的生产方式与传播途径;文学教
育的经验与教训;作家队伍与写作姿态;文体与语言的嬗
变;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和传统性继承;文学中“东与西”、
“南与北”、“城与乡”的呼应;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
关系;文学过渡期、转型期的特征,等等。总结这些经验,
我个人建议持三种研究姿态:一是历史;二是良知;三是
学理。要充分地掌握、梳理乃至重新审视资料,对那些经
过包装的史料,应采取严谨的态度辨其真伪。要把自己摆
进去,因为我们也有过渴念,有过挫折,有过高尚灵魂的
一时毁灭,烟波数度,不能不对知识者与社会的关系有批
判性的质疑和反思性的拷问。学理往往是“无情”的。
研究“共和国文学50年”,自然不是去写政治史、
思想史,而必须以作家为主体,先有作品,才有作家和其
它,其基点和着力之处当在文本,不是这样那样的桂冠。
现在“名家”、“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和实际有相当距
离。依我看,一部好的文本,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本,
大体上应具备四个维度:一是反映民族命运和苦难的历史
维度;二是切近和把握生存状态的自然维度;三是拷打灵
魂的本真维度;四是与神性相遇的超验维度。而对于作家
来说,主要看两条:一看是否有原创性,不是既重复别人
也重复自己,缺少建树;二看是否将艺术推向极致。研究
当代文学,对作家要有恰如其分的定位,切忌搞照顾,“
排排座,吃果果”。
平心而论,“共和国文学”尚处于初级阶段,过渡时
期。从早年不间断的运动到当今非正常的浮躁,都显示了
“过渡”的性征。经历了太多的风雨,面向新世纪,我们
的文学的主题词仍是寻求———寻求对现实的回应力,寻
求新文化的突进力,寻求文学想象的空间,寻求处理虚构
的艺术,寻求与大师对话的可能性。寻求是艰难的,选择
是痛苦的,但过程是美丽的。如今文学的边缘化是正常现
象。我们在边缘站立与创造,正是为共和国文化作贡献的
一种方式。 杨匡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