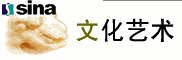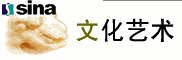叶永烈
最近,我在采访王造时夫人郑毓秀的时候,从一包手
稿中见到一封发黄的信。打开一看,竟是史良在1951年写
给王造时的信。当时,王造时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遍求
良医未得,史良在信中为他介绍了专治这一难症的医生。
王造时和史良同为“七君子”,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本
身就弥足珍贵。王夫人告诉我,在“文革”中遭抄家,王
造时书信被红卫兵们弃满客厅,随风而逝,这封信是偶然
“劫后余生”,更为珍贵。
我在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的时候,她拿出冰心在三
十年代写给梁实秋的信件给我看,使我十分惊奇。我问她,
如此年代久远的信,梁实秋怎么还一直保存着?她告诉我,
平日,梁实秋的信件颇多,但是他只把认为值得保存的信
件放在专门的箱子里。不论是在八年抗战,还是他匆匆离
开大陆前往台湾,他都带着那一包信件。所以这批珍贵的
作家书信,得以保存。
书信,也是作家著作的一个部分。书信不像文章,在
写信的时候往往不是为发表而写,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日
后会公开发表,所以书信往往更多地披露真情。我曾评论
过《傅雷家书》,以为就思想内涵而言,是傅雷最重要的
著作———尽管傅雷是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但是他的几十
部译作只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而已,并不反映他自
己的思想,而《傅雷家书》却是他自身思想的真实写照。
作家以笔耕为业,所以往往作家也最勤于写信。韩菁
清回忆说,梁实秋写信又多又快,“倚马可得”,须臾之
间便写好四、五封信。梁实秋与韩菁清相恋时,虽然天天
见面,梁实秋仍每天向她“面呈”一封文笔优美、散文式
的情信,因为他以为,心中的深情不是口头所能表达的。
然而,书信不像文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手头留
有剪报,也就保存下来了;书信则是寄给别人,并不发表。
信寄出之后,你手头也就没有这些书信了。收信人看完信,
常常一丢了之。尤其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信,几乎很难
寻找。所以,书信最易散失。除非请收信者把你的信寄还
给你———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了。《傅雷家书》所收的
是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由于傅聪非常注意保存父亲的
信,而且他远在英国伦敦,红卫兵们的“铁扫帚”无法企
及,所以傅雷的这些反映他内心世界的珍贵家书得以传世。
戴厚英在不幸猝世之后,平常就留意保存母亲书信的女儿,
编出了《戴厚英戴醒母女两地书》,披露母女俩浓浓亲情。
韩菁清保存了梁实秋写给她的所有书信,我帮她编成了一
本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清书信选集,分别在上海和台
湾出版。
最近,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内中也包括书信。
我的信件甚多,最多时一天收到二、三十封信。我所写的
信,当在万件以上。然而,我早年的信件大都散失,能够
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文革”后的书信,倒是保存了一部分。这是因为当
时我写文章、写书,都习惯于用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一
是怕邮寄时遗失。有了一份底稿,也就“保险”了;二是
作品即使发表或者出版,报刊、出版社编辑总要作些删改,
而保留的底稿则是作者的原作全貌。正因为这样,我养成
了夹一张复写纸写作的习惯,所以在写信时,凡是以为重
要的信件,也就用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样,也就保存
了不少书信。
自从我改用电脑写作,信件也用电脑写。尽管朋友们
以为电脑写的印刷体信件“缺乏亲笔信那种亲切感”,我
仍“我行我素”。用电脑写信,也就在电脑软盘中留下“
底稿”。
这样,我居然保存着自己的大批书信。我遴选了若干
有发表价值的书信,收入文集。通过这些书信,有助于了
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某些作品的写作
背景和经过。
这次经过整理,我也找出我收到的诸多信件,如陈望
道、冰心、韩素音、柯灵、秦牧、徐迟、华罗庚、苏步青、
戴厚英、庄则栋等等写给我的亲笔信。内中,高士其以及
傅雷之子傅敏、马思聪之女马瑞雪写给我的信,都有几十
封之多。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
件,也竟然有十几封……
在整理时,我发觉一件憾事:起码有一半的作家,信
末日期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不能不对作家书信
的写作年份进行“考证”———常常只能断定是“八十年
代初”之类,难以确定准确年份,除非信封尚在,而且所
盖邮戳年份清晰。倒是夏鼐的信,不仅每信都写明年份,
而且总是连“19××”也不漏。这大抵是他作为考古学家
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
在我收到的诸多信中,最可珍贵的是两封信:
一封是《浙南日报》编辑部的信。那是我十一岁的时
候,念小学五年级,写了一首小诗,第一次投稿,收到平
生第一封信。信末,只盖着《浙南日报》编辑部的图章。
这封信经历了“文革”抄家,仍幸存于发还的“抄家物资”
之中,凭着信的笔迹,在编辑部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当
年写这信的老编辑杨奔。从此,我把杨奔视为恩师,因为
是他扶掖了当年作为文学幼芽的我,使我的处女作得以发
表。
另一封是陈望道先生的信。那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给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
一书最早的全译者陈望道先生去信,请教若干问题。他亲
笔回函,认真地给予答复。前些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
上海着手出版《陈望道文集》。当编者得知我手头有陈望
道亲笔信,即赶到我家,用照相机翻拍。据编者告诉我,
陈望道先生得以保存的书信很少,所以这封信很珍贵。后
来,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
本来,越早的书信越少,越近的书信越多。然而,这
次编选书信却发现,八十年代的书信,远远多于九十年代。
内中的原因是随着电话的普及,大都通过电话交换意见,
书信也就越来越少了。如今,我每天除了收到赠阅的杂志
之外,很少收到信件。所以,电话的发达,几乎“消灭”
了作家书信。当然,也可以用录音电话录音,但是把录音
进行整理,所得的只是一问一答而已,跟当年作家亲笔信
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最近由于E-Mail的使用,又使电子书信时兴起
来。只是由于国内的E-Mail普及率不高,特别是作家中用
E-Mail的人不多,我的E-Mail大都发往国外。另外,E-Ma
il大都是电报式的,行文简短,再也没有当年作家书信的
“韵味”。
看来,作家书信的“消亡”,已成“大趋势”。不知
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还能出版几本作家书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