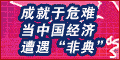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非典洗涤政府思维 政府措施果断勇气从何而来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0日12:41 南风窗 | ||||
|
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自述:我在非典的日子 怀念大医叶欣 谢谢这些平凡的名字 本刊记者橡子 《南风窗》在上一期“窗下人语”中,针对广东、香港的“非典”风雨,发出过自己 4月20日 在我们看来,2003年的4月20日,是此次防治“非典”斗争的一个关键日子,亦将写入中国公共管理的历史。那个晚上,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于当日下午召开的介绍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的新闻发布会的实况录像,人们明白了一些带有几个标志性的事情: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国务院已经果断决定将非典型肺炎列入我国法定的传染病进行依法管理。 二是,北京确诊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和收治的疑似病例,较之以前公布的数字成倍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三是,国务院决定,从明天(4月21日)开始,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接轨。 四是,针对“非典”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孟在当天提出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的请求,两天后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接受)。 五是,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些建议,中国给予高度重视,“这对推进防治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卫生部新任党组书记高强语)。即使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和山西列为旅游警告地区,也“表示理解”,“希望这种(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能够继续下去”(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语)。而就在不久前,无论是3月27至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北京列为疫区,还是4月12日再次将北京列入疫区,对这些重大情况,卫生部对公众均没有任何形式的公告。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的专家组考察报告指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说:“今天没有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4月16日下午,该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专家组直言不讳地批评“北京的军队医院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公布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专家组组长Alan Schnur认为,“北京SARS病例的实际数字会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Wolfang Preisier博士说:“我建议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公布所有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观察对象。这样有助于建立信任,减少谣言。” 自4月20日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再也没有哪个部门或官员说出类似下面这样振振有辞的大话了—— “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在4月3日召开的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郑重宣布); “大家不都是很健康吗?北京市市民不都是很健康吗?大家可以想一想,非典型肺炎在广东最初的病例,可以追溯到三四个月前,而在这几个月间,每月到中国大陆旅游的人都有七八百万,在座各位所在的公司都组织了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旅游者来中国大陆旅行和旅游,有几个人感染上了疫情?”(4月4日,鉴于一些国家政府就中国非典型肺炎发出旅游劝诫,国家旅游局一位副局长在外国〈地区〉驻京旅游及民航企业代表处人员参加的吹风会上说) “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4月10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如此肯定) 勇气从何而来? 4月20日之后,中国抗击“非典”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系列措施,海内外均给予高度评价。中央免去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务,被海外媒体视为“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和对各级官员的“一次灵魂深处的震撼教育”,认为此举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决心与时俱进、塑造执政新风气和新形象的努力,不会因为若干官员的官僚习气和墨守成规而打断。 毋庸讳言,西方媒体对前一阶段中国某些部门和地方官员缩小甚至隐瞒疫情真相、有关医院公然弄虚作假的做法进行“讨伐”,引起一些国际社会的恐慌与不满,严重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国际形象,“隔离中国”之声出现,不少国际活动遭到“杯葛和抵制”。 尽管中国有关媒体驳斥了“隔离中国”声浪中的不实之辞,但显然,对外界的批评,中国领导人采取的不是抗拒,不是讳莫如深,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从批评中汲取“破釜沉舟的力量”,正视问题,断然处之。正如“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吴仪副总理所强调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对重大疫情的透明度不提高,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应允许宣传机构如实而客观报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对前一段时间政府与传媒沟通不够,应作出道歉。据香港媒体报道,吴仪主管商务、旅游、卫生等,由于“非典”的蔓延影响到这些领域,她虽然不分管港澳台事务,但要求广东省直接与香港建立疫情通报渠道,无须按以往惯例通过中央,显示了灵活和务实的风格。 《南风窗》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从十六大顺利实现新老交替开始,增强忧患意识就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一个特色。2002年9月18日,江泽民主持召开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全体会议时就提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繁重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要向全党同志十分鲜明地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十六大报告的结尾也提到了“忧患意识”。观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活动,亲民色彩和忧患意识一直交相融合。他们在抗击“非典”中有如此的决策勇气,绝不只是为了“应对外界压力”,而是内源的、内生的,那就是执政为民、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危的高度责任感。 政府理性的崛起 领导人的果断决策十分重要,但我们在抗击“非典”中更大的收获,也许是在于整个政府思维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昭示着政府理性的崛起。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其责任不能虚置。问责必须到具体的人,而不能仅以一些虚化的理由来搪塞; ——一个人民的政府,各级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而不是对上级的面子和喜好负责。那些脑子里惟独缺乏群众意识的官员,理应深思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叫“人民共和国”的内涵; ——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甚或就不告诉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长官意志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未知的复杂,政府的理性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害责怪政府,但他们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 ——因为“有限的理性”,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垄断”话语权利,“垄断真理”。意见的平台必须开放; ——在一个全球化影响越来越深的世界,国际参与与合作是无法拒绝的。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言,“在全球化时代,合作是战胜新疾患的惟一办法。” 而在更深广的层面上,“非典”风雨中政府行为的调整,可能标志着一个“公共管理”时代的来临,昭示了“治理时代”的先声。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治理(governance)”。和传统的“政府统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理论认为,“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如果说“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的目的则在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指出,“统治”由政府行为组成,其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以国界之内为限;“治理”则是指由公民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其权威不一定是政府机关,而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范围可以是特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 “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这是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和政治家的流行口号。在他们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提出,国家现在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所有问题了,新治理的核心是公民社会。 从中国政府防治“非典”的措施来看,“治理”已经隐约可见。从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领导人的讲话来看,“公共利益最大化”是他们明确而坚定的要求,人民健康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对于中国内部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积极寻求了国际合作,可以说,政府不再将自己看成惟一的权力来源。医疗机构、专家组、世界卫生组织都参与了治理活动,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在一些社区,自愿性的公民团体主动分担了原来一直是政府独自承担的责任。有些地方的医学专家因为不同意官方机构的判断,坚持己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这说明,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已经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之外的其他管理方法和技术。透过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安排,国家的权力在向社会回归,“执政为民”的另一面就是“还政于民”。 企盼公民文化的觉醒 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们感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也亟待培育。从无端的恐惧到“非典”病人擅自离开隔离区,从谣言蜂起到盲目抢购,我们看到,当社会遇到危机挑战时,个体如同分散的马铃薯,无法凝聚成起理性的气氛。这和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发育不充分、公民文化建设相对薄弱大有关系。而当社会的力量远远弱于政府力量时,公共问题的解决又只能听凭政府,陷入旧的循环。 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公民文化的建设,或许有“善政”,不会有“善治”。而公民社会发育的前提,又在于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和维护。我们不可以设想,一个只是忘带了身份证或者暂住证的公民,在城市行走时经常会被派出所的干警抓走,稍有意见就殴打,收容——在这样的气氛里,能够生长出自尊爱群的公民意识。 中国的传媒炒作过许许多多的名流明星,但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谁挺身而出,发挥公共人物的影响,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当李嘉诚为香港的医护人员捐出100万个橙的时候,我们得知,在外商务出差的中国富豪,包下私人飞机回家。他有这样的自由,这对他的企业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区别只在于,他只能想到自己,他是富豪,但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可以拔走一座山。”在全球防治艾滋病的征途上,我们就曾经看到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将为艾滋病筹集资金作为近乎专职工作的大明星,看到过黛安娜王妃抱着一个身患艾滋病孩子照相,让更多人减少对患者的歧视和恐惧,看到过染上艾滋病的篮球明星约翰逊在电视屏幕上讲述如何防病,看到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公开承认他的儿子已死于艾滋病。然而,在抗击“非典”时,我们的英雄基本上都是战斗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的医护人员。 我们赞赏政府理性的崛起,更企盼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两者结合,善治可期。
订短信头条新闻 让您第一时间掌握非典最新疫情!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非典型肺炎防治专题 > 正文 |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