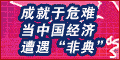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地坛医院隔离5天全记录:一边是天使一边是伤痛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09日14:30 南方周末 | ||||
 与地坛医院一样处于“抗典”一线的中日友好医院,一个医生正在照顾病人,病房里鲜花正在盛开。贺延光/摄 地坛医院,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首个定点医院。如果把正在肆虐的非典比作一场风暴,那么,这里无疑是风暴的中心。5月2日至7日,本报记者鼓起勇气,走进这一“与世隔绝的神秘之所”,用5天120小时的时间,记录了这里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恐惧、勇气、爱与坚持。目前,本报记者正处于接触疫情之后的“隔离”观察阶段。本报编辑部期待他平安归来。 □本报驻京记者林楚方 2003年5月2日上午9时20分,一辆面包车从警戒线里快速冲出来,头也不回。车里两个人神色慌张,眼睛直视前方,口罩几乎可以把眼睛盖起来。 “吓死你了!”警戒线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一边将被冲断的红线接好,一边冲着冒烟远去的车子骂,“不就是这里有非典吗!” “在他们眼里,北京地坛医院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口院子里的空气可能就会致命。” 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是给医院送物品的,刚开始连胡同都不进,打算把东西就卸在马路上,现在能送进院子就是好同志了。” 自从3月26日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个非典病人以后,这里的形象就已经注定——“这是常人远离的地方。”一条长长的布线将医院“紧紧”地围起来,原先员工可以走的通道已经被死死地封住,医院和外界的通行被严格限制在一条狭长的小路上。 狭长的小路外面是安定门外大街,里面是北京地坛医院——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首个定点医院,医院里住满了非典病人,263名。 5月2日一早,本报记者走进这个非典风暴的中心地区,用5天的时间全面地观察这个“与世隔绝”、甚至有点令人心惊胆寒的神秘之所,记录下其中不为常人所知的生活,记录下这里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记录下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恐惧、勇气、爱,与坚持。 悄然而下的泪水 5月4日,地坛医院2楼的走廊里,老院长冯惠忠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在各个科室转,身子有点颤抖,“国难当头,让我回来,我就得回来。我现在得先了解情况,再协助制订方案。” 冯惠忠,63岁,地坛医院原院长,已经退休。上午还在菜市场买菜,突然电话打来,要求立即到卫生局报到,有关领导要他返回医院协助工作,一定要“提高准确诊断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医务人员感染率。” 二楼,长长的楼道尽头,院长办公室,现任院长刘建英对记者说,昨晚她躺在沙发上,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我梦见护士高兰在被抢救,我一下子就醒了,发现衣服都湿透了,可能是吓的,因为脑子里老是转着这些事,还好就是一个梦。” 高兰是北京地坛医院第五个被非典“放倒”的护士。刘建英拿出一张纸巾,快速地擦眼泪,“如果让我许个愿,我最大的愿望是,到最后喝庆功酒的时候,地坛医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少……我今天怎么了,在年轻人面前也这么激动。” 一楼,护理部办公室,主任陈征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四川一个护士要求义务到地坛医院来帮助治疗非典,她说她会用呼吸机,而且会英文,如果答应,她会在第一时间赶来。 陈征婉言谢绝了,“不能让太多的人卷进来。”刚放下电话,手机又开始响,没接手机,又一个电话打来,“七区护士长要进行调整,工作一定要有序,不能乱!” 陈征的下属说,“她都56岁了,如果她提出退休,谁也不会说出什么,可是在这个关头,即使是66岁76岁,她也不会走。” “我在传染病一线干护理工作38年,从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场面。”陈征的嗓子有些沙哑,“看到那些年轻的护士病倒了,我难受呀!她们都像我的孩子一样!”两行泪水立刻流下来。 如果说非典是一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最前线的那些战士,无论是院长、医生还是护士,每一个被采访的人,都会在记者面前情不自禁。 “市里要每个收治非典病人医院的一线人员进行休整,可是我们实在抽不出人去呀,领导就说,护理部要把它作为政治任务完成。我们只有千方百计调4个护士过去,可是她们,她们……” 陈征再次在记者面前老泪纵横,几乎说不下去,“可是……可是第二天她们就写了请战书,要求回来,说任务已经完成,已经有媒体采访了,她们心里难受,想回来——大家都累,为什么就只有我们休息呢?” “你知道上甘岭的那个苹果的故事吗?大家都渴,但苹果只有一个,如果她们吃了,别人就吃不到,所以大家都不想吃。道理就这么简单。”被派去休整的护士的一个同事说。 陈征继续念叨,“有两个被感染的护士刚出院,她们就跟我说,主任,我们一定要好好休息,休息好再回来!这些护士太好了,她们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她们为什么感染?因为连续工作好几天,每天就睡几个小时,抵抗力一下子就下来了,就被感染了,我心疼呀!”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得一个轻一点的非典,能够有个躺下来休息的理由,而且身体里有了抗体,好了以后可以继续往前走。”七区护士长陈帆说。 3月26日:战车被发动 地坛医院就像一辆战车一样,在波及全国甚至世界的非典风暴中高速向前行使,“它从开始发动就不能停下来。只能一直往前走,直到‘风暴’停止,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传染病医院,很可能将战斗到非典最终消失的那一天。”刘建英说。 这辆战车从3月26日被发动起来,那天,北京地坛医院开始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 “25日上午,我们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共同研究收治非典的有关准备,后勤要把病房清理出来,护理部配备护士,医务科要配备医生,总务科负责后勤保障,包括卫生、床位和床单以及防护物品的到位。” 当晚,北京地坛医院来了第一个病人。4月2日,国际劳工组织的阿罗约被送了过来。 随后,北京的疫情变得日渐紧急,4月10号,这里开辟了第二个病区,但很快就收满人。“当时感觉,疫情好像还会发展,可能还要开新的病房。”刘建英说。 4月17日,北京市卫生局紧急动员,要求将地坛医院作为收治非典的专门医院,其他的病人全部转走,只收治非典病人。 “现在大家觉得传染病好像只有非典,实际上,我们医院几乎收治了所有的传染病,包括麻疹、水痘、猩红热、流脑、腮腺炎、出血热等等。”医务科科长陈一凡说。 地坛医院从此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隔离历程,有人比喻,从17日开始,每个员工都是地坛医院这辆抗击非典战车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谁都不能被“拧”下来。如果原先还存在着侥幸,“非典是少数人的事,那么从那天开始,不幸将属于每个人。” 18日、19日两天,原先住在这里的404个病人被转到了其他医院,按照收治非典的要求,病房进行重新改进,仪器进行安装,由于这里收治的本来是传染病病人,所以还必须进行消毒。 从4月17日开始,地坛医院动用了其所有的资源,门诊4月24日被关闭,“门诊、保健科、B超室的大夫、护士,所有能进到病房的全部进到病房,其他医院的支援也陆续到位。” 在开始收治的过程中,由于口罩不够,医院总务科科长到处乱转,有一天,“他竟像孩子一样高喊,‘市政府给了我两万米纱布!’” 4月21日晚上,这里转来了第一批病人,以后每天开出一个病区,每个病区当天就收满了,直到开到第9个病区。 逃跑的与留下的 4月20日,正当所有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时候,食堂临时工集体提出离开,病房部分卫生员也要提出离开。 “医院可以一天没有院长,但不能一天没有这些人,垃圾没有人清运,食堂没有人做饭,整个医院就可能瘫痪。”主管的郭副院长说。 “你们得先把今天早上的饭做好,医院几百口子病人还有职工也要吃饭。” 上午10点半,郭被要求和他们对话。 “第一,非典不是那么可怕,我们医务人员都在里面,首当其冲的不是你们,是医务工作者,你们连病房都不进。 “第二,国难当头,我们有责任,你们也有责任,这里面住的都是你的同胞,也许有你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们不尽这份社会责任也可以,但别怪我无情,一分钱也领不走! “第三,如果留下来,该加钱加钱,该补助补助,而且我们承诺,如果因为在这里工作而得了非典,你们的医疗我们都包了。” 最后,大部分临时工走了,骑着自行车,挑着铺盖卷,再也没有回来。“我也理解他们,他们都很不容易,不能要求人家跟正式工一样,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才这么不讲理的!” 也有人最初就没打算走,一个49岁的老卫生员,在地坛医院工作3年了,“医院正是困难时候,怎么能给人家撂担子,再说,护士那么小都敢进病房,我儿子都娶媳妇了,我怕什么呀。” “能留下来的人就是好同志,现在他们干得都很好,真的。”郭说。 “另一个难题是,职工住在哪儿?医院没有职工宿舍,员工住在北京的四面八方,下班以后大家都累得不行,而且很多职工周围的邻居不愿意让他们回去。”刘建英说。 “谁家里有在地坛医院工作的,几乎就不让上班了,孩子是幼儿园的,因为妈妈是地坛医院的,也不让送了,在普通人心里面,我们这些人就是高危人群。必须给他们找个住处。” 这也是来自一线的声音。如果没有住处,大家的工作就没法干了,“我们是干传染病的,治疗非典是我们的职责,但最不应该发生的是,如果自己感染了,把家里人也搭上。” 可是宾馆很难找,一个宾馆的员工听说地坛医院的人要过来住,人一下子几乎跑光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将问题反映上去,上级通过行政命令,才解决了部分同志的住宿问题。” 在他们最终住下的那个宾馆,一个姓谢的副经理说,“现在国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全靠他们了。” 护士:剩下的只有意志 5月4日,北京地坛医院,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隔离病房,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要从这条走廊进入到隔离区,非典病人是通过另外一个通道才能进去,只有他痊愈后才可以享受这个走廊。 走廊的旁边就是隔离区,可以看见病人在里面活动,从走廊里走,每转一个弯就是几个病区,走进4病区,先要进入半污染区。 在这里,进去的人被要求戴上两层口罩,穿上一层薄薄的防护服,一层橡皮手套,手套要把袖子套在里面,戴上帽子,再穿上一件更厚的防护服,再套上一层橡皮手套,再把眼罩套在头上。 所有进到病房里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大家看不到对方的任何痕迹。护士小李也穿着同样的装束,她开始给病人抽血,一喘气,哈气把眼罩模糊了,“我经常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给病人抽血,有时要扎几下。”小李的头几乎贴在病人的胳膊上。 护士做什么工作?“我们除了要做好医生布置的基本工作,吃药、打针、打点滴、抽血等,最多的是护理。”小李走到病房外,有点发抖的样子,长长地喘着粗气,“现在心率有100多次,氧饱和度经常比病人还低。别说干活,穿上这身衣服就剩喘气了。” 按照规定,非典病人是不能有家属进行护理的,所以,病人的护理工作全由护士完成,一个病人躺在床上,似乎很艰难,小李用勺子将药放到他嘴里,把水也喂进去。 “这还是好的,很多重病人,就在床上大小便,我们要帮他们倒,有时,还要帮病人擦洗干净。有时想,我还剩什么,可能剩下的只有意志了。”说着,小李将一个小桶端走,“其实,病人最可怜。” 和许多护士一样,小李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没有休息,一位医生说,“护士最辛苦,现在护理量大,因为危重病人多,而且穿着那样的衣服,连喘气都费劲,别说干活了!” “我走出病房里最大的愿望是能喝上一瓶冰镇矿泉水,可是还不能喝,因为要尽力避免去厕所,这身衣服,穿上以后就不好脱下来,脱下来就不安全,一天要穿至少6个小时。”护士文静说。 “看到她我们就难受” 护士高兰被感染了,住到病房里,小姐妹们来看她,一看到她就哭,高兰也哭,“她肯定接受不了自己得非典的事实。” 领导嘱咐让去看高兰的人不许哭,“可是谁也忍不住,平常都是在一起的,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呢!” “看到同事倒下是最难过的,我总觉得下一个就是我,但又想,大不了就是个死嘛,最受不了的是对家人的愧疚感,本来每天就让他们提心吊胆的。而且我们结婚才4个月,要是我死了,他再找一个就是二婚了,多对不起人家呀。”护士刘晶说。 刘晶的老公是律师,“刚知道要去非典病房,就给老公打电话,电话里就哭了,我说我以后照顾不了你了,也照顾不了你父母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说,‘要不你别去了,我养活你。’我说那还行?现在辞职不就是逃跑吗!要走也要干完非典再说吧。要是有下辈子,我一定不干护士了,但是这辈子的事情不能欠着。” 刘晶继续说,“我经常会泪流满面,哭完了还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电话里说‘没事,挺好的’,放下电话又接着哭,有时我会想,怎么一夜之间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穿着防护服,还戴着眼罩,手套,这还是我吗?原来在肝炎病房,当时觉得环境很脏,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干净多了。” “来支援的人可能干几个礼拜就回去了,我们却要一直干下去,有两个来的人给自己画‘正’字,画到几个,她们就回去了,我们也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7区护士长陈帆说。 “非典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和爱人和孩子说话都隔得很远。原来八小时就下班,工作中同事之间有隔阂,一回到家就都忘。但现在整天都在一起,工作到这份上,好像经常有‘无名火’。有同事有时凌晨3点下夜班后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说话,因为有委屈。” 6区护士长徐秀坤说,“我们区住了几个其他医院的护士,她们说当时看着身边的人倒下了,就特别难过。我们也是。我们一边聊,一边忍不住哭,大家都是高危人群,说不准谁已经被感染了,只是没发作出来而已。” “其实,我们是女人,就哭哭而已,到时候该上还是要上。”一个护士长说,“我们还是有自信的,我们医院有很好的防护措施。而且大家都知道谁不能马虎,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5月5日,上午9时,6病区,一个护士走出来,小心地脱掉防护服,动作自信而沉着,负责消毒的护士走过来,用喷壶喷遍她的全身,包括鞋底。 她走进护士工作站,和同事们打着招呼,从口罩里隐约可以看见她在笑。护士们互相还开着玩笑。 医生:“如能控制非典我可跳楼” 麻醉科医生刘子军坐在记者面前,显得有些瘦弱和憔悴,他被强迫休息。 “我是地坛医院有名的‘毒王’,你也戴上口罩吧。”说着,刘子军把口罩死死地系住,麻醉医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负责插管,和病人几乎零距离,“我也不知道插了多少管,有的病人,你插上去,他就给拔出来,接着又插。” “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妈妈也感染了非典,开始他们还是在一个病房,但是后来由于母亲的病情严重,他们就分开了,有一次小男孩冲着我们喊,‘叔叔,阿姨,求你们救救我妈妈吧,求你们了!’那种声音真是撕心裂肺,我当时就发誓,一定要把他妈妈救活。 “我把小孩带到他妈妈面前,我说‘宝贝,拉着妈妈的手’,我觉得,当孩子拉着妈妈手的时候,妈妈就会感到有力量,我对他妈妈说,你看,孩子还这么小,你忍心走么?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一定要配合我们!” 没过几天,男孩的母亲就走了,“我感到自责呀!我一想到那个孩子喊‘救救我妈妈’,我就想哭,你知道医生入门都要读誓词,可现在我觉得,当你听到12岁孩子那声‘救救我妈妈’时,你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医生。” 地坛医院收治非典的前一阶段,麻醉工作基本上是由刘子军一个人做,“当时不知道非典战役会打这么长,这么大,所以希望参与的人越少越好,因为感染的几率就可以固定在小的范围。” “其实,我们老主任也非常难,他60多岁了,你知道,这个年纪感染了意味着什么,我才40多岁,感染了还能从病房里走出来,但他要是感染了,后果就难说了。但有一次插管,我要上,他用胳膊狠命地顶我,把管子从我手中抢过来,当时谁也没有说话。他可能是在想,‘我都60的人了,怕什么。’他这是舍老命陪君子!” 有人说,经常会看到刘子军衣冠不整地从一个病区到另一个病区。 刘子军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医护人员倒下,“因为有一个人倒下了,对所有人的打击是难以形容的。” 刘子军说他现在要休息几天,“我下了决心要休息,因为长时间疲劳就增加感染的机会,不能让别人感到‘你看,就是他冲得凶,他最先倒下’。所以,我一定不能倒下,要不谁再向前冲的话都会有所顾忌。” “你说害怕吗?当时肯定没有怕的感觉,就是条件反射一样冲进去,就是救人,你不进去,病人脑缺氧,几分钟就完了。你迟疑一分钟,甚至几秒钟,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可能永远走了!” “我承认,我不是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有基本职业道德的人。在这个时候,医生和战士没有区别,让你上去,你就得上去,要不你就是逃兵。”医生焦以庆说。 “也许我被感染,也许病得很轻,发发烧就过去了,也许我就死了,各种可能都有,就好像士兵去战场,活着回来是英雄,但也可能就牺牲了,但上战场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医生黄克林说。 “如果非典能被控制住,我立刻就可以跳下去。”刘子军甚至这样对记者说。此时的刘子军在他的宿舍,3楼。 病房:真实的声音 李华就躺在面前,他的嘴离记者的嘴只有1米多,“你还是站得远一点,医生说我是突发期,突发期传染性强,你还是站在门口吧,那里通风。” 他是某大学的大四学生,“我一定可以活着出去,我还年轻,可以挺住。告诉我的同学们,我在这里很好,医生护士对我都很好,让大家放心。”李华戴着呼吸机,感觉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跳。 李华最大的欣慰是,“我没有传染给我宿舍的哥们。”他一个哥哥最先被传染,就把他也传染上了。 4病区,王杨和母亲在同一个病房,“我父亲在一家医院住院,我妈妈、我和我哥哥去陪护他,没想到大家都染上了非典,我父亲已经先走了。” 王杨的哥哥,48岁,在同一个病区的另一个病房,护士说他病情很严重,已经上了呼吸机,危在旦夕。 “老头子走了就走了,可是把两个儿子弄成这个样子,大儿子还不知道死活……”老太太再也说不下去,失声痛哭。 “您是医生吧?”一个病人问记者,因为记者和医生一样的装束,“你能帮我打听打听我爱人在哪里吗?我被确诊后转了几个医院,听说我爱人也被隔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她也感染了,她一定被感染了,我们天天在一起。” 这个病人说,他最害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他爱人,“听说一旦我死了,将就地火化,如果她还活着,只能看到我的骨灰,她非哭死不可,如果她死了,我能出去,我要是只能看到她的骨灰,我也没必要活下去了,如果我们都死了,能不能呼吁一下,把我们骨灰放在一起?” “我现在感觉很难受,我就想看看孩子,我知道不能看他们,他们也被隔离了,大儿子已经死了,我感觉也不好,恐怕日子也不多了,二儿子也够呛,老伴已经先走了,得了非典以后,大家谁也没见过谁。”病人李田说。 “我现在感到很孤独,很恐惧,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也没有手机,我想出去,看看不戴口罩,露出脸的人!你能帮我吗,医生?”他也把记者当作医生了。 非典已经被列入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当一个病人被确诊后,他将看不到一个亲人在他的旁边,除非他的亲人也染上了非典,而且被分在了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病区。 “由于转到地坛医院的重症病人多,并发症多,有基础疾病的人多,所以我们目睹死亡的机会要多得多。” 一个医生说,这次非典爆发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家族性,一家子一家子的住院,一个家庭有一个人感染,往往大家都可能遭殃。所以,他们也目睹了一个个家庭悲剧,在整个社会灾难面前,这些悲剧令人心碎。 后非典时刻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珍贵的,一个在地坛医院采访的摄影记者讲述他的一个经历,有一天凌晨3点钟,他在一个病房门前,看到一个危重病人睁开了眼睛。 “我感觉他善良极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不知道,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否还能睁开,也许他在享受着每次睁开眼睛的乐趣。” 一个护士在临走的时候,将一个病人的氧气调到“5”(表示氧气量),护士走了,他看着冒着的气泡,轻轻地将氧气调到“8”,“也许多3个自己就会更安全一些。” “也有的病人可能很绝望,明明配合治疗就可以好起来,但是你刚把管插上,他就给拔出来,他们最可怜!心理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还难受。”一个医生说。 当我从隔离区走开的时候,还要通过那条长长的走廊,可以不用任何防护装置,甚至不用戴口罩,感觉空气都是新鲜的,可以说,这个走廊属于每个健康的人。 而病人则从另外的通道进去,只有他痊愈后才可以享受这个走廊。 “我把它叫作生命走廊,每当我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都会深呼一口气,呼气的滋味已经久违了,这里的空气是干净的,从这里走出去就意味着你活下来了。”一个来采访的记者说。 截至5月7日上午9点,已经有34个人从这个走廊走出来,有25个人在恢复期被转走,还有19个人从另一条通道走进病房,就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条长廊的阳光和空气,他们永远地走了。 而在全国,截至5月6日10时,有4409个人从另外一条通道走进像地坛医院这样的隔离病房,其中包括883名医护人员,已经有214人永远不能走出那条象征着健康的走廊。 非典风暴将注定留给人们黑色的记忆,一个个医生护士倒下,一个个家庭因此而解体。一个在地坛医院采访的记者因此呼吁,“能不能为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灾难死去的所有人,那些医生护士和非典病人降一次半旗,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注:文中的病人名字均为化名)
订短信头条新闻 让您第一时间掌握非典最新疫情!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非典型肺炎防治专题 > 正文 |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